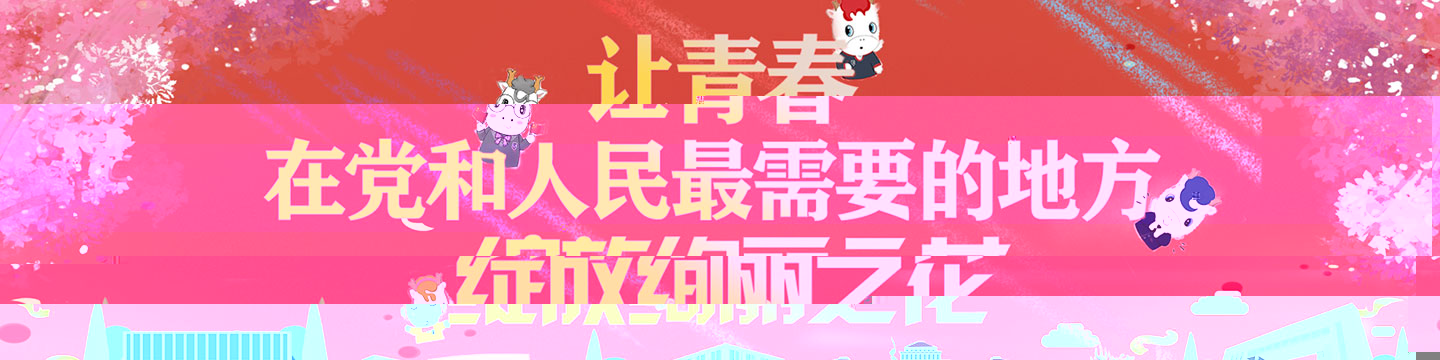日前,國務院《關于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健全包括個人所得稅在内的稅收體系,逐步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進一步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發揮收入調節功能,适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這些内容引發社會熱議,尤其是“高收入”的劃分标準。應當指出,《意見》當中并沒有提出高低收入的劃分标準,社會上廣為流傳的“12萬标準”恐怕缺乏依據。我國從2006年開始,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納稅義務人自行申報個人所得稅,這一标準是否适用于十年之後也有待讨論。
應當看到,《意見》當中這些提法是着眼于調節收入分配。目前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之大已是不争的事實,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雖然經過連續幾年下降,2015年我國的基尼系數仍然高達0.462。當前要求稅收政策進一步發揮公平收入分配作用的呼聲非常高,但是稅收政策并不是萬能的,公衆要求稅收公平收入分配的同時,往往忽略其局限性。隻有對稅收政策在公平收入分配中的優勢和局限性加以充分認識,才能揚長避短,更好地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
稅收政策是國家的一項政策手段,任何一種政策都存在有局限性,政策效果不僅會受宏觀經濟環境的制約,更重要的是任何政策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就有一些固有的、與生俱來的缺陷,稅收政策也不例外。國家的宏觀經濟目标對稅收政策的價值取向起到指導性、方向性的作用。如果國家的政策目标偏向于經濟的快速增長,即追求效率,那麼對于市場幹擾較少,稅收中性較強的流轉稅就是國家的優先選擇,但是流轉稅對收入分配具有逆向公平的作用。如果國家的政策目标偏向于促進社會的公平,那麼所得稅、财産稅等直接稅就會成為國家的優先選擇。
流轉稅、所得稅、财産稅三大類稅種在公平收入分配時各有不同的效果,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流轉稅最終由消費者承擔,在客觀上減少了消費者的财富總量,因此流轉稅對收入分配可以起到一定的間接調節作用。由于稅負轉嫁的存在,流轉稅調節的方向與調節力度的大小都難以确定。需求彈性小的商品的稅負容易轉嫁,而需求彈性大的商品的稅負相對難以轉嫁。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彈性要小于奢侈品的需求彈性,因此流轉稅的稅負主要由中低收入者承擔,這對收入分配起到逆向公平的作用。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流轉稅的累退性,即使是高收入者,他們在一定時期内的消費量也是有限的。由于流轉稅普遍采取比例稅率,所以随着收入的增加,流轉稅具有累退性,低收入者的稅負要高于高收入者。
所得稅是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最重要的稅種,但是所得稅是在初次分配基礎上的二次調節,如果初次分配本身就十分不公平,所得稅能起到多大的調節作用就要打個問号。世界上主要存在分類征收和綜合征收兩種個人所得稅征收模式,關于這兩種方式的優劣,曆來存在争議。在分類征收的模式下,按來源對所得進行分類,每一類所得分别計算納稅。這種模式沒有考慮到納稅人的綜合收入水平,并且往往存在費用重複扣除、稅率設計不合理等問題。綜合征收模式則将納稅人的各項所得比較全面的考慮進來,理論上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較強。但是綜合征收模式的制度設計非常複雜,稅收成本很高,負外部性十分明顯。更重要的是,在實際當中綜合征收模式并沒有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公平收入分配的效果。美國是典型的采用綜合征收方式的國家,但是美國的個人所得稅制極其複雜,稅收成本也十分高。《1994年聯邦稅則》中關于聯邦所得稅稅務細則的就有6400多頁,聯邦所得稅的征管需要480種稅務表格。1980年美國的基尼系數不到0.3,2015年調整後的美國家庭基尼系數已經高達0.462。高額的稅收超額負擔使得美國的經濟學家提出了“單一稅”的設想(例如Robert E. Hall等人)。
個人所得稅的比重一方面反映了個人所得稅稅負的輕重,但是在另一方面反映了個人所得稅的調節能力。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很低,始終在10%以下,我們不禁要問:如果個人所得稅隻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小稅種,那麼個人所得稅的調節能力何在?公衆和媒體一旦提及個人所得稅,目光往往就聚焦于所謂的“起征點”(實際上是工資薪金所得的費用扣除标準,出于語境的考慮姑且稱之為“起征點”),似乎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越高,對公衆的讓利也就越大,按照這種邏輯鍊條個人所得稅幹脆取消掉豈不更好?稍有常識之人馬上就會意識到,個人所得稅不能取消。
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其實最重要的是政策目标的問題,個人所得稅的目标到底是什麼?所有的稅種都有籌集财政收入的功能,隻要承認稅收扭曲的存在,客觀上就有調節的功能。那麼個人所得稅的定位是什麼?如果定位于公平,那麼在最終結果上就要讓高收入者的稅負比低收入者更高,這是一個常識問題。但是現實是複雜的,考慮個人所得稅的定位時,國家治理與地方政府主體稅種的因素恐怕繞不過去。
公衆對于“12萬收入分界線”的關注其實反映了當下對收入分配不公的焦慮,個人所得稅的調節重點不應當落腳到工薪階層上,所得稅不能蛻變為“工薪稅”。不過應當認識到,既然要調節收入分配,那麼對收入按照一定的标準進行高低劃分就是必然的。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收入”,不能僅僅是工薪,應當是全口徑的收入;高低收入的劃分标準,應當考慮到地區間的差異性。
政府幹預經濟有多種手段,稅收政策隻是其中之一,各種政策各有所長。應當在宏觀經濟目标的指導下制定具體的經濟政策,制定政策時要做到統籌考慮,使各種政策能夠協調配合形成合力,減少政策間相互掣肘的情況。在稅收政策調節高收入的同時,更應當關注财政支出在增進低收入者福利方面的作用,使宏觀經濟政策在收支兩個方向同時發揮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作者:任志偉,bevictor伟德官网2015級财政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