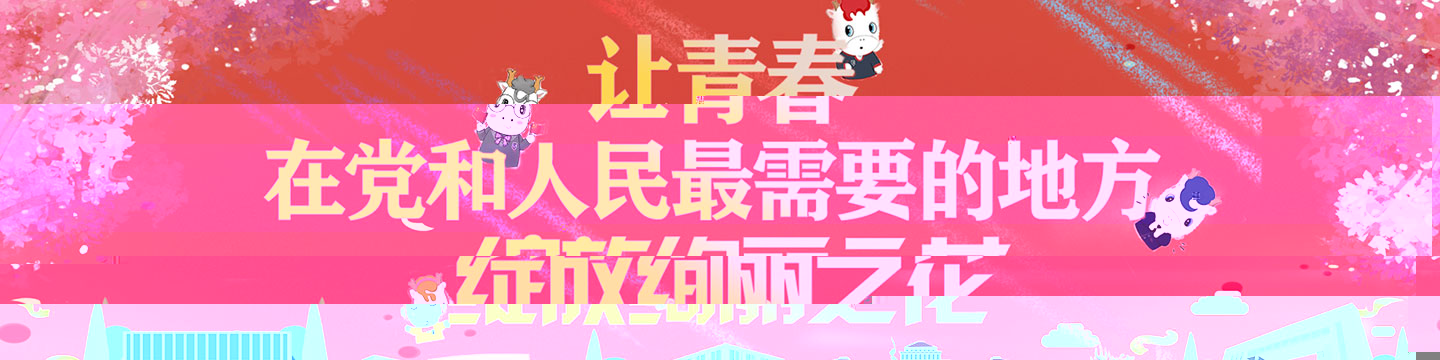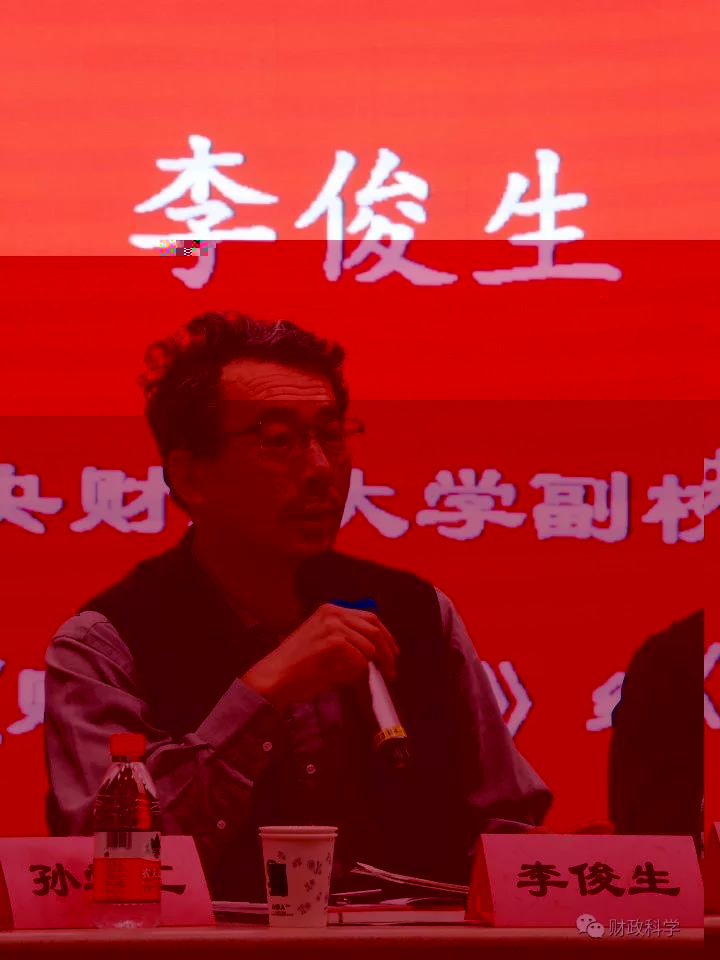
為深入學習和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探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财政理論的創新發展,中國财政科學研究院《财政科學》編輯部主辦了“學習十九大精神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财政理論創新”專題研讨會。此文為bevictor伟德官网副校長、《财政科學》編委李俊生的發言内容,全文将刊發于《财政科學》2017年第11期,并于近期在中國知網(CNKI)進行網絡首發,敬請關注。
我想結合我們财政理論工作者的使命和責任來談談學習十九大報告的體會。
十九大報告除了散見各處的有關财政改革與發展問題的描述以外,還集中用了78個字專門闡述我國建立現代财政制度的方向性問題,雖然字數不多,但是内涵豐富。實際上,十九大報告講的新時期我們國家經濟、社會、人文方方面面的發展都離不開政府财政,因為财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未來我國财政改革發展任務還極為繁重,任重道遠。
改革開放近40年我國财政改革與體制、機制建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是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依然很多,特别是在我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前提下,我國财政改革與發展也相應地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作為一名财政理論工作者和财政學專業的教育工作者,我覺得我們也有責任、有義務為我國在這個新時代的财政改革與發展貢獻我們應有的力量與智慧。所以,我想從我們的使命和責任這個角度談談學習體會。
一、新時代财政理論工作者的曆史使命
十九大報告中有幾個地方特别值得我們關注,其中一點就是,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經曆了“站起來”“富起來”兩個時代,現在進入了使中華民族強盛起來這麼一個“強起來”的新時代。報告中還用了專用的一個詞彙來講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和主要矛盾,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時代跨越,社會基本矛盾發生了變化,過去,我國長期面臨着廣大人民群衆的需要與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生産能力不足的矛盾。現在的主要矛盾好像表現為産能過剩,即現在不是生産能力不足了,而是過剩了,我們開始進入了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不穩定的過程。總書記在報告中對此做了非常精辟的論述,在這裡我就不贅述了。我想說的是,在這個曆史發展的新階段,财政理論工作者和财政專業教育工作者的曆史使命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依然是要為建設民主富強文明的國家服務、為人民的福祉貢獻我們的聰明才智,為建立适應新時代需要的财政理論和财政體制與制度服務。
二、新時代财政理論工作者的責任
如上所述,進入新時期,我們的一個重要曆史使命就是要建設強大的中國,使我們民族更強大,在世界民族之林發揮我們作為一個大國、一個強國應有的作用。為此,我國不僅要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硬實力”,而且也需要進一步增強我國的“軟實力”。作為财政理論和教育工作者,我們的主戰場應當是在國家“軟實力”建設領域,我們的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構建立足中國實踐的,能夠有較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的中國的财政理論。為了完成這個時代賦予我們的曆史使命,我想我們至少肩負了兩個方面的責任。
第一個責任就是為我們國家的财政治理能力建設,為财政改革與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持。
這些年我國财政理論建設存在的重要問題就是我們很少立足中國的實踐構建适應我國需要的财政理論,比如我們沒有認真地梳理我們政府、包括财政部在國家治理過程中的職能是否和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相适應,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沒有認認真真做過這方面研究思考。所以,當政府及其财政部門感覺到工作力不從心的時候,我們沒有理論去支撐。我這樣講并不是說我們财政學就是為财政部服務的,如果這樣理解就是狹隘的。政府财政是為國家治理服務的,财政部門也是為國家治理服務的,财政部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一個組成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财政理論工作者沒有科學、客觀地解釋财政行為規律,沒有科學、客觀地為政府财政職能的設計提供理論依據,這就是我們财政理論在立足中國财政與社會發展實踐方面做得不夠的地方,就是我國财政理論建設方面的一個重大的缺陷。我們财政理論對實踐支撐做得不到位的地方還很多,我們可以列舉很多例子,比如這幾年我們往往感到财政改革的實踐大大超前于我們的理論,就是說我們在理論上沒有能夠對現實給予令人信服的描述。我們為什麼做不到這一點呢?這就是我們财政理論工作者自身有問題,是理論建設跟不上國家發展的需要的重要表現。我最近在财政基礎理論領域做一些努力,立足于我們中國的實踐,針對我們中國的需要構建科學的、具有解釋力和預測力的财政理論。長期以來,我國實際上是全盤引進了西方的财政理論,盡管我們不能否定這個理論對我們經濟改革發展起到了很多的積極作用,但是總體上看,西方的、以英美财政理論為代表的主流财政學理論是建立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實踐基礎上,難以解釋我國的财政實踐,更不用說為我國的财政政策提供科學可信的理論依據了。我國現行的主流财政理論實際上是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30年代,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40年代就由我國财政學先輩從西方引進來了,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由于經曆了内戰,經曆了朝鮮戰争,經曆了一系列波折,沒有能很好地梳理、消化、研究這樣一些理論。現在我們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一個和平建設的時期,一個能力建設的時期,我覺得在這個時期我們有理由,也有必要來梳理我們的理論,為我們國家的國家治理提供我們理論的支撐。這是我國财政理論工作者的第一個責任。
第二個責任就是我們财政理論界應該為我們國家“軟實力”的增強貢獻我們的智慧。
總書記在報告中特别強調我們要講好中國的故事,向全世界講好中國的故事,這是我們“軟實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講好中國的故事?比如講财政的故事,現在我們還用西方的财政學範式講我國自己的财政故事,包括大學教科書中還在套用英美的财政理論範式講财政聯邦主義,講中國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财政關系,這個理論範式顯然是不适應我們中國的需要的。這樣講中國财政的故事是講不好的。所以,我們财政理論界有責任構建我們自己的範式,講好我們中國自己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增強我們中國的軟實力,我們财政理論界其實是責任重大的。我們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在這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分析中國财政的現實、講中國的故事,所采用的卻不是基于中國的财政實踐建立的理論,上個世紀八十、九十年代我們有國家分配論這樣一個理論,但是國家分配論由于其本身存在缺陷,很難講好我們改革開放之後實行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财政故事。
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一再證明,财政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引導我們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向上、向前的重要的關鍵環節。最開始是在城市,80年代初我國将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這個解放了當時農村的生産力模式引向城市,解放城市區域生産力。因此,我們當時就有了“包”字進城。所謂的“包”字進城就是把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這套方法應用到城市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中,而這個“包”字進城實際上就是從财政改革開始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過去我們的财政叫“建設财政”,這個“建設财政”怎麼解釋?我們财政運行模式是企業所有的收入都要上交财政,企業所有的支出(包括更新改造的支出)都由我們政府财政來安排,這是最初我們财政的狀态。我們要改革這種财政運行模式,改革這種預算模式,改革這種支出模式,改革這種收入模式,比如利改稅就是從财政開始。從财政改革開始還有一點就是政府财政其實是切出了一大塊資源給非政府部門,從而來拉動市場經濟、來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這種改革走到了盡頭,兩個比重嚴重失衡。所以,才有了1994年分稅制财稅體制改革,分稅制之後财政又恢複了元氣,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火車頭,我們又開始拉動國家的經濟向前、向上發展。現在我們又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怎麼來解決發展的不平衡問題。總書記講精準扶貧,我看各行各業都講精準扶貧,但是真正能夠在精準扶貧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還是政府财政,銀行做不到,因為銀行是以盈利為目的,如果在精準扶貧中讓它發揮主力軍的作用,那有可能又回到改革開放之前的四大專業銀行的回頭路了。所以,我們中國這些發展的曆程就是個很好的故事,如何把這個故事向全世界說清楚,這其實也是梳理我們自己的思路。
要想說清這些故事必須有一個說故事的模闆。有的小說家喜歡先預測好結果,這是一種模闆;有的小說家願意憑感情用事寫,寫到什麼程度就寫成什麼樣,但收不住筆了還要回過頭來重新構建一下這個小說,這也是一種範式。财政理論用什麼範式講中國的故事,讓全球相信我們這個故事是真實的,相信我們這個故事是有感召力的,相信我們這個故事對全球的發展中國家是一個模闆,這就是我們的使命和責任。
注:轉自《财政科學》微信公衆号,原文網址 http://mp.weixin.qq.com/s/b-x3m2Hv2GUYFcpkBB_Nwg